
在今天早上,也就是大年初二真正去世之前,诗人江南就曾传闻他几年前就去世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如此悲痛,但一位西方文学艺术协会的领导人在脸书上写了“告别诗人江南”,然后就搁置了……出去了。于是,人们纷纷表示哀悼。我确信江南叔叔还好好的,因为几天前我刚和他通过电话。但我还是半信半疑,于是我打电话给他在芽庄的学弟诗人陈赞威,在电话里,我听到诗人陈赞威在骂脏话。整整一天后,这位“告别诗人江南”的人才回到脸书上……更正了消息。

我第一次见到诗人江南是在芽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拜访的人,心里非常紧张。然后,他出现了,热情友好。我最喜欢的是,临走前我和他打招呼时,他直呼我的名字。
之后,有一次他去波来古,我组织了一个诗歌之夜,他担任主角。我记得,他一出现,全场的人,大部分是师范学院的学生,都站起来,围在他身边……表示敬意。一位朋友坦诚地说:“我以为江南叔叔……是个烈士。没错,大家都学过《故土》这首诗,现在才亲眼见到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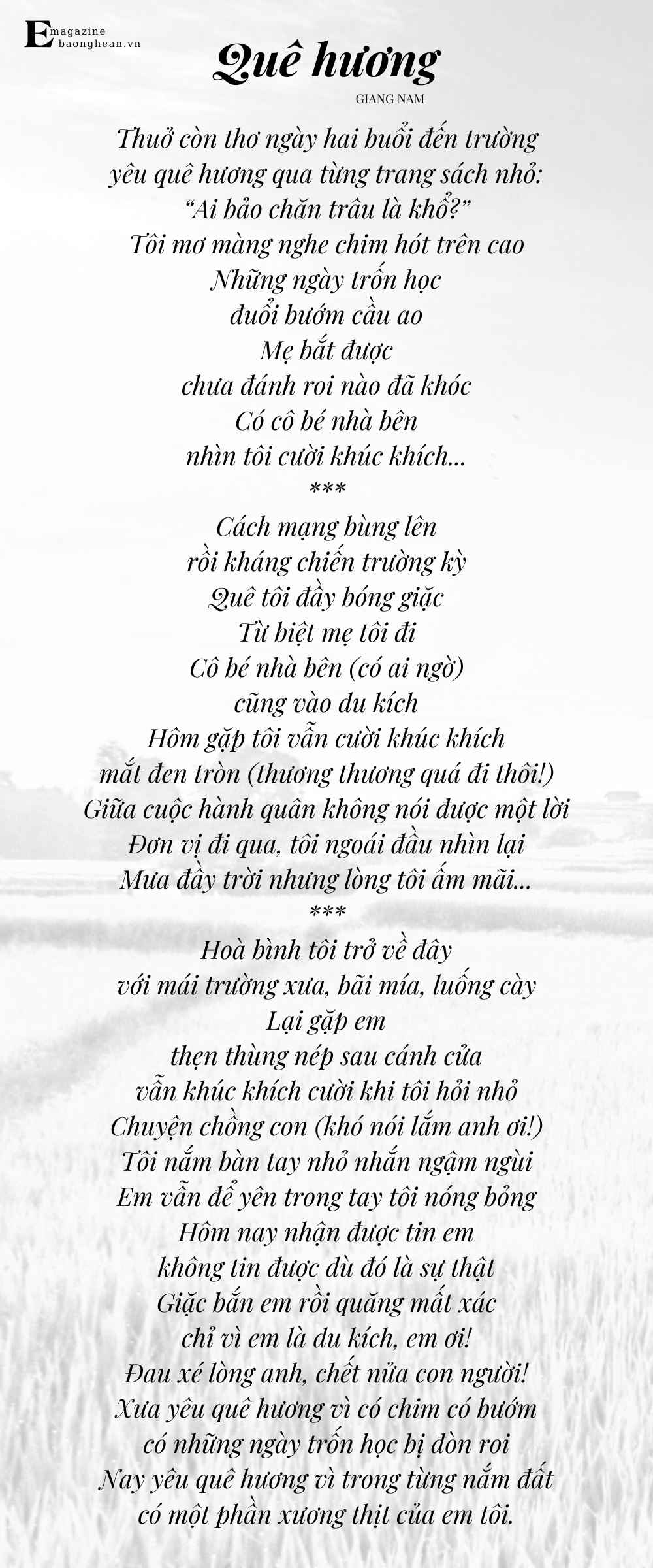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透彻理解这首诗,正如我写过一篇关于访问他在芽庄的家的短文时所证明的那样,看到她,那个老游击队员,做鱼露卖,我买了几升吃,作为礼物,许多朋友过来想知道,那个游击队员……牺牲了,在哪里?
后来我见到他的次数多了,特别是他当庆和文艺协会主席的时候,我在嘉莱文艺协会工作,当时庆和文艺协会和嘉莱文艺协会的关系还挺密切的,他当了省副主席之后就没那么密切了,不过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昨天我看见他挥舞着自行车比赛的旗子,你要不要跟着蹬一会儿,他笑了,我就坐在车里跟着兄弟们蹬了一会儿。

自从他退休后,我经常见到他,因为他经常旅行,而我也经常去芽庄。他的行程大多与文学活动有关。当时我是越南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中部和西原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委员会主席,所以我们当然经常见面。
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在岘港的一个文学会议上见过面,当时正值一场国际足球锦标赛。在此之前,他不得不接受一次大手术,先切开胸腔接通血管,然后从手臂上取一条血管连接到心脏主干,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因为他的动脉粥样硬化阻塞了。他张开手,给我看他手臂上延伸下来的疤痕。他患有冠状动脉阻塞。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会放支架。但他的阻塞非常严重,需要十多次切开才能完成。于是,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切开他的身体,从他的腿和手臂上取血管,然后接通,就像在补贴时期我们给轮胎装内胎一样。在此之前,几位法国医生亲自给他检查过,他们……都摇了摇头。因为他年纪大了,已经七十多岁了,正如医学文献所说,他已经不需要手术了,而且他仍然很虚弱。
无论如何……他都会死。当有人建议直接手术时,他立即答应了。而且手术出乎意料地成功。据说,当时的法国教授们……仍然摇着头,因为他们听不懂。之后,他变得非常健康,头脑也清醒。正常人到了那个年纪都会糊涂,更何况是个诗人呢?人们常常看不起诗人,认为他们老了,脑子有问题。但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曾担任富庆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文艺协会主席,更早之前,他还担任过作协《文艺报》的主编。而且他精神矍铄,举止文雅,步态端正,笑声爽朗,甚至还会谈论……女人和女孩。因此,他非常渴望观看晚上6点半和9点的比赛,而跳过了深夜的比赛。可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睛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昨晚的比赛是谁赢了?

记得当时亚太诗歌大会举行的时候,我们到达内排机场,越南作家协会派车来接我和他,两人同机。当时他已经87岁了。但坐在车里,看着他的脸,看着他拎着包钻进车里,拒绝我帮忙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已经是个老人了,再过三年他就90岁了。回来的时候,还是我和他一起去机场,我送他到值机口,然后就告别了,因为他的登机口和我的不一样。虽然工作人员让他签了一份保证书,但仍然没有人会想到他已经那么老了。
回国途中,我写了一篇关于他和他那场奇特手术的文章,发表在《健康与生活》报上。有一天,他打电话过来,笑着说:“我刚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高兴得都笑哭了。哦,你在哪里看到的?哦,庆和省卫生厅厅长看了报纸,看到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就送了过来。”我那个年纪,应该叫他叔叔才对。我看到几个比我大的人都叫他叔叔。但我早就叫他哥了,就趁机在电话里“献上”了。他笑着说:“叫我哥就行。”我说:“那你再活13年就好了,等你100岁了,还得让我们这些晚辈跟着你。”他又笑了,把手机号码告诉我,说以后会经常打电话过来聊聊。我问他是否有电子邮件,他读了,但说这是他侄子的电子邮件,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他会告诉我......

然后他告诉我,一个朋友跟他夸奖他:“真高兴,现在不用写作不用思考,直接玩就行了。” 他立马说:“妈的,我得做,再懒也要每天读几个小时书写。” 虽然我知道我写得不好,但现在我写作是为了……锻炼,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作曲。话虽如此,我还是偶尔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诗,也看到他出色地回答电视采访。他告诉我,他那些老朋友,年纪大了,性格就变了,吃了很多苦。其中一个朋友把老婆孩子赶出去独自生活,他去看望的时候,看到他们过得多么悲惨,却也给不了什么建议。还有一个朋友每天早上到处跑,看到什么就捡什么,他最喜欢的就是……婴儿尿布。捡完之后,他会去找哪个有邮箱的人,然后把尿布扔进去……
今天早上,他安详地去世了,享年96岁。我记得那天,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游击队员,后来去芽庄制作家族鱼露,先离开了他,同样非常安详,她躺在吊床上休息时去世了。他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在医院躺了几个月,然后去世了,我听说他去世时也很安详。
我远远地和他告别,讲了一些关于他的琐事,他的性格,他的求生意志,以及他非常乐观的态度。也正是因为他的乐观,他才活得长久,而且非常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