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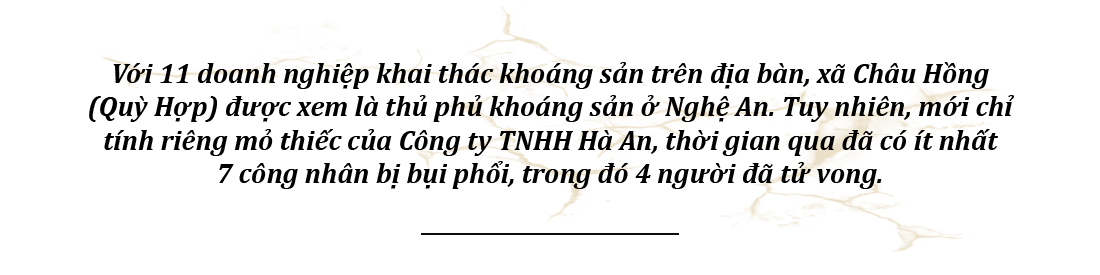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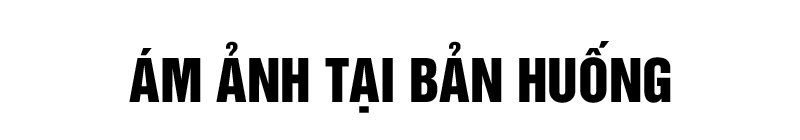
“Can也死了!现在只剩下我和我两个人了。”这是七月初的一天,住在归合县周鸿乡香村的张文头给我发来的信息。这条信息让我震惊,因为就在几天前,为了写这一系列文章,Can还是我拜访和交谈的对象之一。
33岁的哈文坎先生和陶先生,两人都曾在周鸿乡的哈安有限公司工作,几年前才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我们到达香村时,坎先生虽然无法行走,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他的一切活动都得依靠64岁的母亲。他原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转眼间就成了母亲的负担。住院期间,家里的所有财产也都消失了。

“一个多月前,我还能在家里走动,但也就十米左右。现在我卧床不起。很多时候,看到孩子呼吸困难、咳嗽,我只能哭,因为我们没钱带他去医院。我们只能等。”我们到Can的母亲Vi Thi Nguyet家时,她哽咽着说道。因为家境困难,Can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没来得及结婚。
父亲早逝,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从小,Can就不得不外出谋生。和Huong村的大多数人一样,Can也上山采锡矿卖钱。2014年,Can申请到Ha An有限公司当工人。这家公司在Can所在Huong村附近的山上开采锡矿。他的工作是钻探锡矿。虽然他整天在锡矿里辛勤工作,但每天的收入只有15万越南盾左右。“每次我这样钻,钻头的粉尘都会直喷到我的脸上。但当时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Can在生前探望他时说道。
从事锡矿钻探工作六年多的何文詹,2020年开始出现持续性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甚至无法握住钻头,于是他让家人带他去医院检查。“去医院一看,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硅肺病,已经无法洗肺了。医生说,这种病是多年从事锡矿钻探工作,吸入过多粉尘造成的。”阮女士补充道。何文詹原本是一个体重超过70公斤的健康青年,但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体重不足30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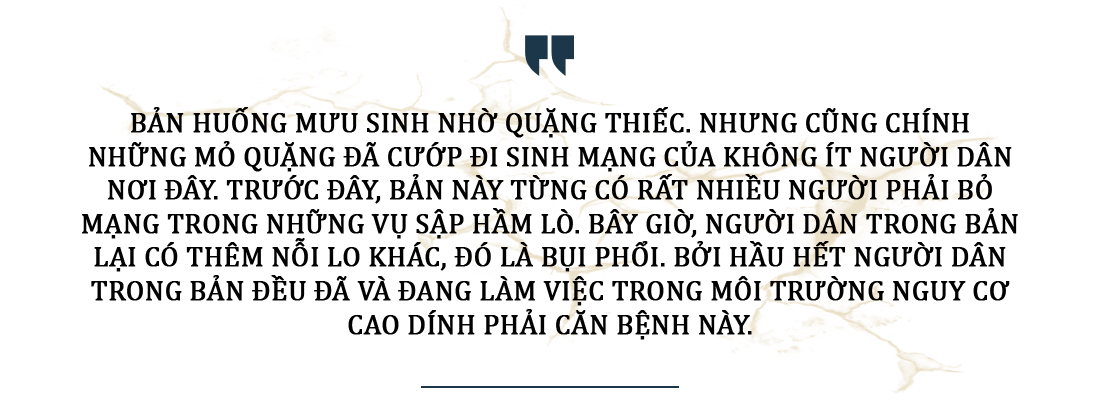

张文涛(40岁)的家离何文坎家只有几十米。然而,几个月来,张文涛一直没能走过去探望同样情况的同事。张文涛说,相比其他人,他很幸运,发现得早,还洗了肺。然而,尘肺病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只能在屋里走动。“每次走十多米,我就感到筋疲力尽,呼吸困难。自从发现病痛以来,我的体重减轻了20多公斤。”张文涛说。
陶先生于2017年申请加入哈安有限公司(Ha An Company Limited)。和詹先生一样,陶先生的工作是在深山锡矿中钻探锡矿。“矿井里通常有很多灰尘。但每次我们钻探矿石时,情况都很糟糕,灰尘飞扬。两个工人挨着钻,但灰尘大到看不清对方的脸,”陶先生说。2021年初,陶先生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Covid-19)。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还患有硅肺病。之后,陶先生辞职了。

“幸好我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尘肺病发现得早。至于其他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现在想想,我后悔自己太主观了。”陶先生说。他还补充说,工作时公司也提供口罩防尘,但大多数工人都不戴,连布口罩都不戴。“其实一部分原因是我主观,没觉得粉尘这么危险。一部分原因是矿井工作很辛苦,戴着口罩或呼吸器呼吸很困难,只能工作一小会儿,就得摘下来。”陶先生补充道。
尽管在这里工作多年,Can先生、Tau先生和其他许多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保险。因此,患病后,他们没有得到公司的任何支持,也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尽管尘肺病被列为职业病。在他们工作期间,公司没有定期组织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因此疾病无法及时发现。
据张文涛先生介绍,仅在他所知的哈安有限公司,过去几年就有7人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其中4人死亡。“这7个人都是锡矿钻工,这个部门是接触粉尘最多的。不过,这7人只是我们所知的周鸿乡的病例。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感染了尘肺病,但他们在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不清楚。”张文涛先生说。
在陶先生列出的7个人中,还有38岁的魏建先生。魏建先生也住在香村,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哈安有限公司担任钻井工人。2019年底,由于工作辛苦、工资低,魏建先生辞去了工作,申请出国劳务。“我去体检申请出国工作时,发现自己得了尘肺病。当时病情非常严重,我根本没法洗肺。”魏建先生说。从那时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住院。住院期间,他呼吸困难,手脚也难以活动,只能由亲戚抬着去医院。

哈安有限公司的一位领导在接受《义安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一些曾在锡矿工作的工人患有尘肺病。“这是因为过去采矿是手工进行的,所以灰尘很大。大约一年前,我们投资了现代化的机械,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他说。
珠丰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文和先生表示,该乡目前有11家矿业企业。“关于工人患尘肺病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一些病例,但当局无法掌握具体情况,也没有统计数据。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保险。”张文和先生说。
仅统计一家公司的生产线,以及居住在周鸿乡的工人,短时间内就有多达7人患上重症尘肺病。与此同时,归合县有80个矿山开采,以及一系列石粉加工企业,工人达数万名。我们联系了归合县的许多机构和单位,但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掌握在这种高风险环境下工作后患上尘肺病的工人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