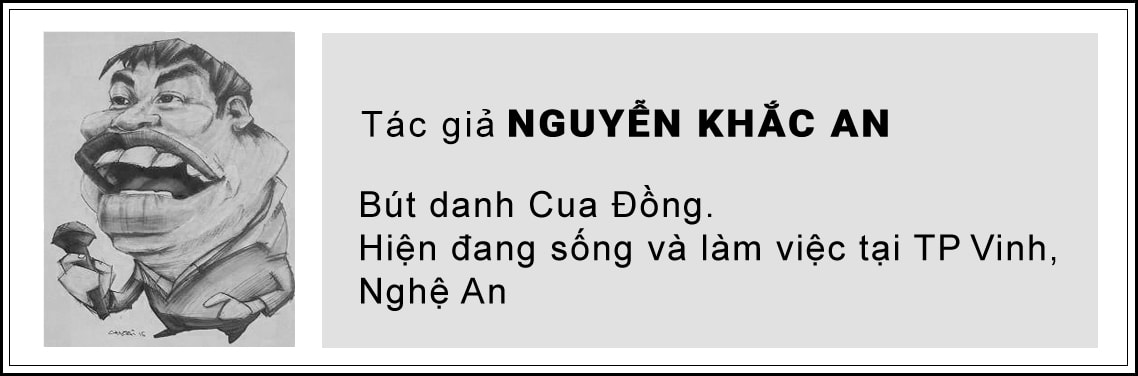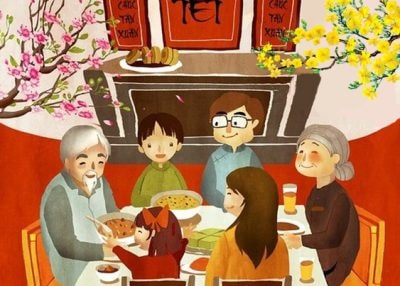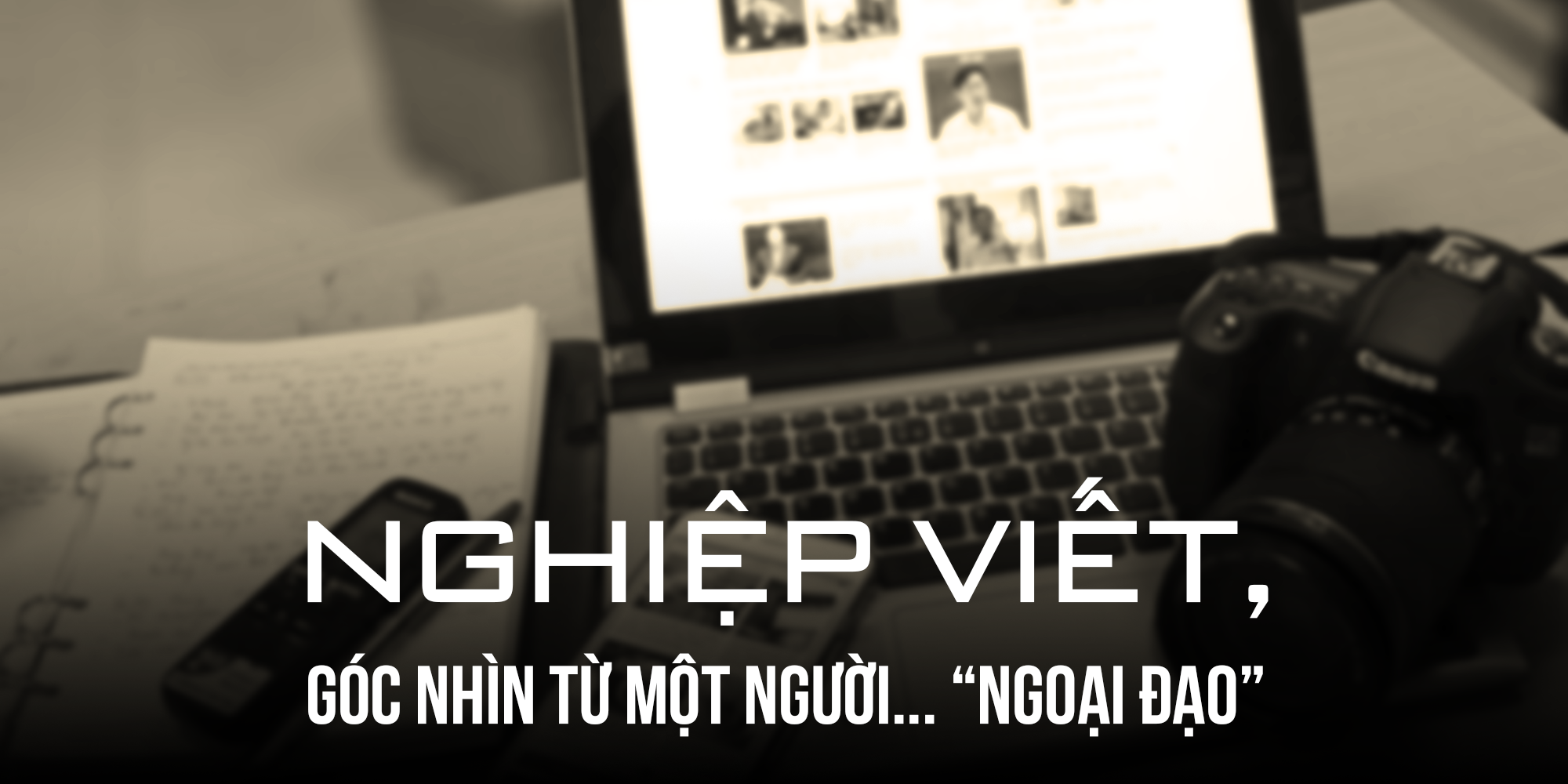
“载多艘船而不沉”
“用你的笔刺向恶人”
(阮廷照)
再过几周,6月21日就是越南革命新闻日了。在社交网络上,新闻爱好者们开始用“框架”来表达对记者的敬意。值此向记者致敬和表达感谢的社会活动之际,我想谈谈这段永恒而艰难的故事。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只是一个“合作者”,文字的探讨如同一个业余作家真诚坦率的告白,一些关于写作的零散想法,也只是局外人的视角和经验,一个纯粹出于热情的写作者。
生活从未停止过一天,它色彩太丰富,魅力太强大,也充满了各种事件。社会分工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稻农、纺丝工,“抄写”人类生活的任务,寄托着那些从事写作的人。写作可以是作家、诗人、记者……当然,写作的空间仍然足够宽裕,让我们这些“业余”作家可以自由体验。
写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它不仅需要健康、智慧,也需要道德;不仅需要道德,也需要勇气;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激情。写作或许并不难,但从来都不容易,它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无数难以言喻的挑战。接受写作这个职业,意味着接受随时随地的辛勤劳动。上班的路上可能出现一条新闻简报,回家的路上可能出现一篇文章的开头,睡梦中可能突然闪过一个诗意的念头……休息,是作家心中不存在的一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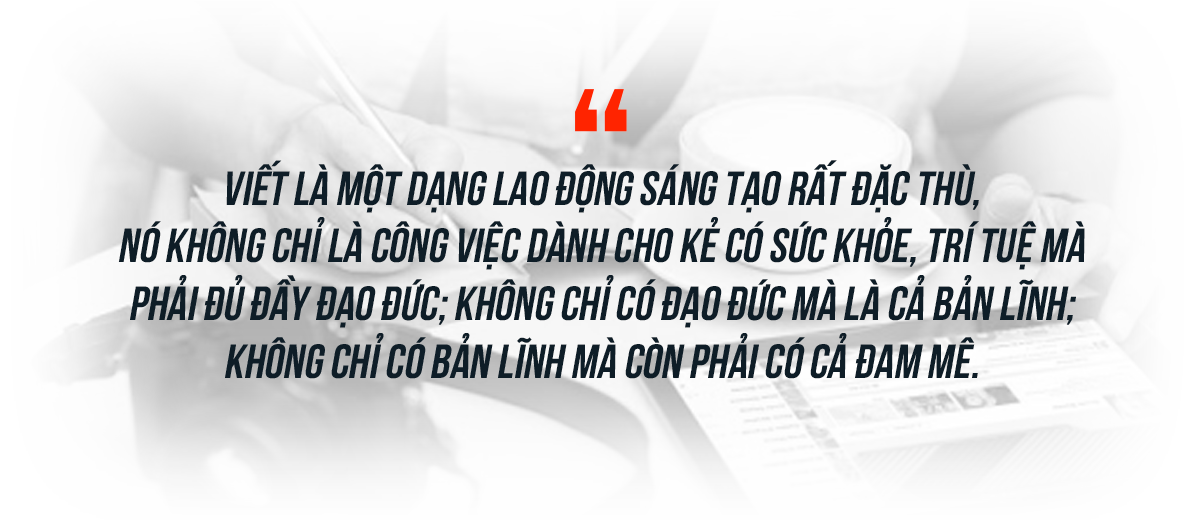
我想起阮攸《翘传》里的两句诗:“若不小心失足,便踏出一步,用家乡的文字呵护自己。” 写作是工具,生活是素材,而作家才是责任的承担者。写作并非儿戏,漫不经心的写作如同玩耍,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社会。作家不断地追问着那些看不见却又挥之不去的问题。将文章公之于众让他的头发染黑,但将这份心血倾注到读者手中,却让他的头发白了。
接收和处理读者的反馈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工作,即使这并非一种艰苦的工作状态,有时甚至有害。责任的持续性导致了工作的持续性。写作是一项需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任何疏忽大意的行为都可能要付出代价。写得不好可以,但尽量不要写得糟糕。写得不好可以,但绝对不允许写得错误。“笔落鸡毙”是作家的口头禅,而非舆论的威胁。当一部作品超越电脑,到达读者手中时,它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作品了。它是报纸、杂志、喉舌的声音,甚至是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必须将自己的作品塑造、挤压和描绘成一个既定的形状。一篇文章没有自我固然不好,但只有自我才是失败的。没有个性的作品是坏作品,但仅仅是个性的舞台的作品也是坏作品。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谐,或许是作家必备且极具挑战性的素质之一。每份报刊杂志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来展现其独特的形象。作家有责任尊重并遵循杂志或报纸的宗旨。谁没有因为文章中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被删减而感到心碎呢?但我们不得不意识到,用心写作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挥笔。那句话,那一期,或许是作者的最爱,却不一定是报纸的最爱。作家必须接受“入乡随俗”的道理。写作并非胆怯之人,也并非粗心之人。写作关乎细心,确切地说是细心,关乎每一个细节。有时,每个逗号都要仔细斟酌。有些报纸被停刊,也有些作家受到处罚。请注意,道路宽广,但我们只能选择一条路——前进的道路,一条充满正义与人性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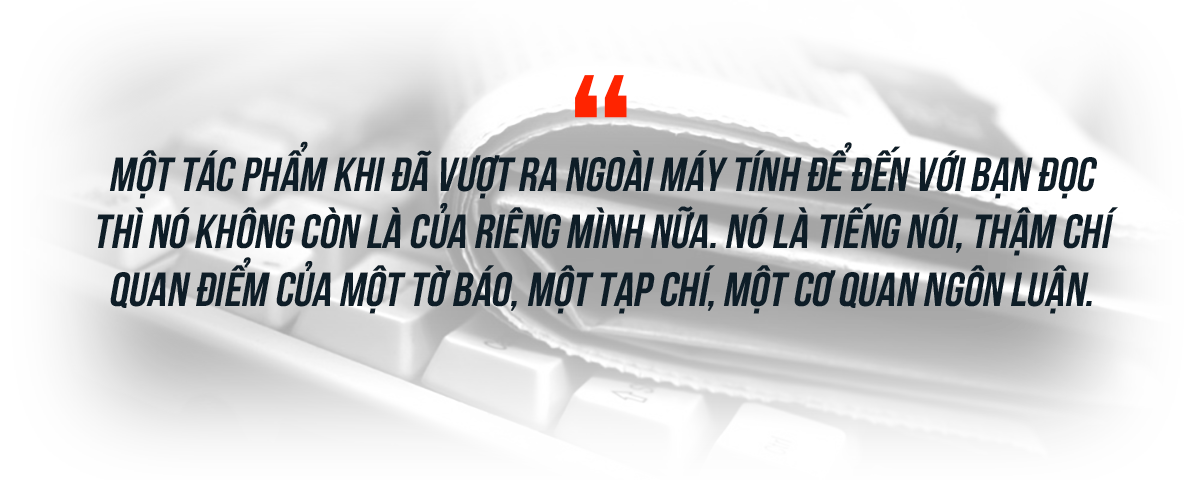
谈及作家的责任,胡志明主席曾指出:“为谁写”、“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完再写什么”。其中,“为谁写”被放在第一位,也是对艺术家和作家最正确的答案:为同胞和战士写”。他还指出,作家的价值“在于活在人民心中,为党的光荣革命斗争作出贡献,服务人民。这是光荣和自豪,同时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作家的义务和崇高责任,要与一切保守主义、停滞不前、落后主义和反革命主义作斗争”。
其实,作家是前线的战士。在国家还沉浸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时,无数作家和记者在举着黑白相机奔赴战场之前,举行了追悼会。如今,他们戴着口罩,脆弱不堪,奔赴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他们坚守在森林深处伐木,足迹镌刻在边境和岛屿上,在那里,生死的界限如同树叶般柔软。
写作时,也别忘了不要混淆大脑的功能和心灵的职责。一篇文章到达读者的旅程是多种因素的综合:问题的热门程度、信息的容量和可靠性、作者的观点、向读者传递的信息、呈现方式以及语言材料。
作家有时不得不面对危险和诱惑,而努力克服这些危险和诱惑,正是真正作家的使命。值此越南革命新闻日之际,笔者想分享一些感悟,以表达一位“突然”爱上写作的人的感激之情。写作很难,但也很有趣。相信我,如果你写作,你就会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