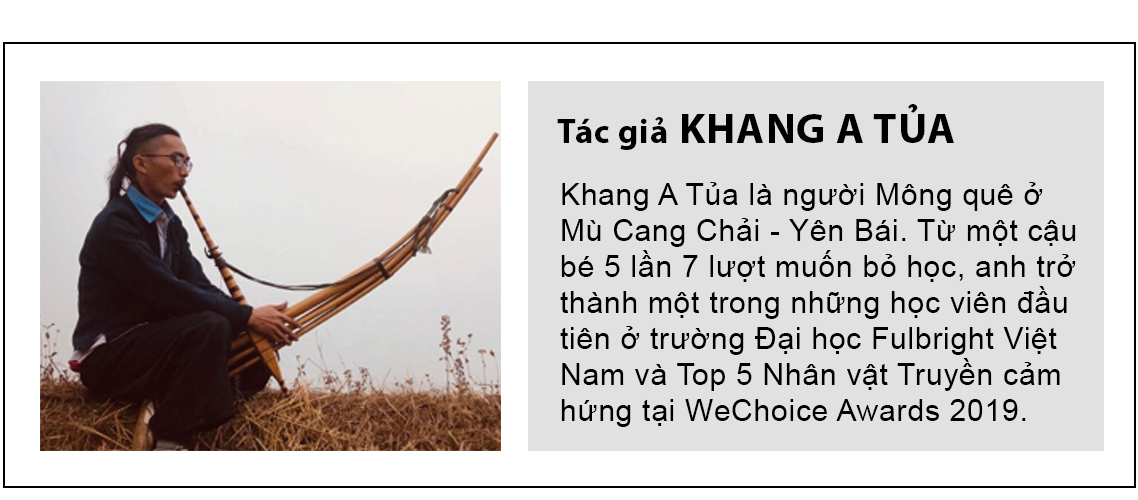尽管电影摄制组竭尽全力,深刻细致地再现了蒙族文化,但《阿福的妻子》和《宝的故事》两部影片都存在一些基本错误。除了本专题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导致对蒙族文化某些具体概念理解错误的原因之外,还有作者在下文中分析的,构建错误的蒙族文化语境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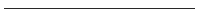

影片《阿福的妻子》(1961)对文化语境的第一个错误建构,在于对一对男女过于轻浮、性感、亲密的形象的再现,而这恰恰发生在春节——一个参与人数众多的公共活动——的正中央。影片中,男女主角成双成对地出现在春节场地的中央,他们或牵着手,或亲密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公共的空间,而根据作品语境中苗族人民的文化原则,这样的场景实属罕见。
需要明确的是,抛包游戏的诞生(要求)这纯粹是为了让男孩和女孩通过游戏来增进感情。女孩们会拿着自己的包,站成一排或一队,等男孩们经过,等到满意了,女孩就会主动把包扔给男孩,并说些类似“Pov tuaj lawm aus,paab txais ov”(包子飞过来了,我的朋友。帮我抓住它。)男孩,带着最大的尊重,不管他喜欢与否,都必须接住包子(或者如果他没接住,就捡起包子),把它扔回给女孩,并回答说,“请稍等”(归还这个包子)。因此,包子是男女之间对话的开始。抛包子游戏(而不是传递东西)表明了男女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足够远,可以抛出一个用碎布缝制的圆形物体,比如包子。因此,在蒙族文化原则中,在春节期间玩耍的男孩和女孩大多玩抛包子游戏,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就像泰国蒙族导演 Xab Thoj 的电影《Ib Leej Tub》中那样。而不是像《阿福的丈夫和妻子》(1961)中那样站在一起做出过于亲密的姿势。


电影《宝的故事》(2006)错误地重现了一场蒙族葬礼。在影片开头宝老母亲葬礼的场景中,摄制组邀请了一个蒙族角色,并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歌曲。然而,这里使用的歌曲却是葬礼仪式中的一首歌曲。胡普利格——蒙族人将灵魂召回肉体,继续尘世生活的仪式。这首歌的歌词是蒙语的,影片中没有字幕,我听了之后翻译如下:
"Ob ploj tsi of rab teb as, yaj tsi of rab ntuj es. Tshuas coj qaib mus o, ruas hu tau tus niam plog nev as yaj tshi 88 rab raj. Coj qaib mus txa tau nus tus ntsuj duab rov qhos qov los。Ob ploj tsi of rab teb,rab ntuj 的 yaj tsi。 Tshuas mus txa tau NWS ve fo los Hu tau tus niam pos li 88 rab raj。
大致意思就是:
“哦,[灵魂]从地球上消失了,无法到达天空。所以[我]带了这只鸡来,是为了把这个女人的88个灵魂部分召回来。带这只鸡来养育她那部分灵魂,让它回到这里[附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歌与葬礼完全脱节,因为对于蒙族人来说,葬礼是把离开死者肉体的灵魂送回祖先那里,送往天上,准备投胎转世到另一个肉体;但这首歌胡普利格这有相反的意思,即召唤活着的人迷失的灵魂回到这个人的肉体中(火车已关闭意思是灵魂回到肉体,继续活下去,这是文化意义的逆转。
我们可以认为,歌词的使用方式胡普利格葬礼是电影团队的一种艺术暗示,暗示宝玉饰演的老母亲并没有死,她会复活,回到电影里。但或许并非如此,因为电影团队并没有充分重视歌词的内容。这体现在他们没有翻译歌词的含义上。胡普利格,与此同时,在另一场戏中,当年轻的母亲,也就是Pao的亲生母亲生下一个女孩时,操着苗语的角色却批评说女孩的出生没什么特别,而剧组在越英字幕中也把这段对话直译得一丝不苟。由此,我们可以排除剧组在这个场景中隐藏艺术含义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是剧组的文化误解。
还需要补充的是,电影《宝的故事》是在河江省同文县松罗乡龙锦村一户苗族人家中拍摄的。摄制组进驻前后,这家人依然正常地生活在那里。同时,苗族人认为葬礼是一种具有深厚精神意义的仪式,绝对不能在家中进行伪装。这或许也是摄制组难以在影片中深入还原苗族葬礼的原因之一。然而,电影中有很多关于葬礼的隐喻,无需直接拍摄真实的葬礼场景,却依然能展现出苗族葬礼的独特之处。


2006年的电影《Pao的故事》对蒙族服饰的刻画存在错误,片中Pao一角有时穿着同文蒙族的服饰,有时又穿着苗瓦蒙族的服饰。这再次表明摄制组对蒙族的误解,因为他们未能明确Pao是同文蒙族人。
如果时间设定在2022年,确实会有蒙族人穿着其他蒙族服饰的情况,但该片是2006年受文化信息部委托拍摄的,根据1997年的作品改编,讲述一个真实故事,描绘的社会是20世纪80年代同文的蒙族人;故事中人物身穿蒙苗瓦服饰,却没有详细说明其穿着原因,说明电影中的服装设计师并不了解不同蒙族群体的服饰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