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范·平,怀念森林的人
(Baonghean) - 哦,奇怪,为什么叫他“思念森林的人”?他还住在家乡,没有远走高飞?有多少人叫过他,叫得对,叫得好:“绿林猛虎”、“召唤泰魂的人”、“挖掘的人”、“复活的人”、“泰学之人”……然而,他却像古老森林里的一棵椴树一样沉默。他怀念棕榈成熟时节杜鹃的鸣叫。他怀念儿时在漏斗状沙坑里找到的蚁狮,任它们打架。他怀念在收获季节吹奏的草笛。他怀念招魂仪式上老僧的祈祷……
带着这份乡愁,他带我回到了他居住的村庄——千岩村。孟千岩村依偎着普济山脉,宁静祥和,流传着陶昆廷和普千岩的传说。他出生在那里,与家乡的许多泰国人一样,经历了家庭的艰辛。他说自己是水牛年(1961年),所以总是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勤奋刻苦,但又慢条斯理、悠闲自得……他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但他仍然能够上学,从未想过辍学。或许,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他为了教育“生死与共”,把自己的艰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为他们树立榜样。华先生(三文平的父亲)14岁时,背着11岁的弟弟和稻米,徒步60公里穿过森林,来到贵州学习读书写字,因为当时他的家乡贵合村没有老师教他读书写字。直到他们能熟练地读写后,兄弟俩才返回家乡。当时正值全民教育,华先生凭借着识字能力,后来被任命为公社干部。
萨姆·文平第一次打开了与家乡的森林、群山、崎岖的道路、茅草屋顶……截然不同的神奇世界,是父亲带回来的几页《小年报》。他知道,除了这个村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大村落,除了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泰族和京族人,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而要走出家乡的森林,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那时,萨姆·文平只能从一个班级到另一个班级学习。老师们只是刚学会读写的学生。教室有时在地板下,有时在房屋的一个小角落里。七年级时,作为省级文学奖的优秀学生,萨姆·文平有机会参加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夏令营。这在这位从未离开过家乡森林的小学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萨姆·文平通过了水运大学(后来并入海防海事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在当时的村里是“稀罕事”。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决定学习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或许,是出于一丝好奇心,以及像年轻人一样渴望探索的欲望?对于一个“丛林人”来说,学习船舶设计和建造,并渴望自己的船能够横渡浩瀚的海洋,这是否很危险?
毕业后,萨姆·文平苦苦挣扎了很久,却找不到工作。直到现在,他还在想,为什么找工作对他来说这么难。萨姆·文平暂时忘记了大学文凭,暂时忘记了远渡重洋的愿望,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重新做回了农民。做过工人和农民之后,他开始在采石场打工,参与锡矿开采,挖柴根,然后和兄弟们从银行借钱买了一台铣床做雇佣工……生活把他淹没了,让他不时地感到悲伤:哦,我曾经是一名模范学生,去过德国参加夏令营,拿到了大学学位……然后就不能离开安良村,离开普哲山脉了。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更大的耻辱,更大的损失,是他是泰国人,生活在泰国人社区,却感觉像个迷失的人。为什么我不能解释一个泰国习俗的起源,为什么我不能念诵一篇祭祖祷文,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泰国的习惯法,为什么我不能为许多懂习俗的老人渐渐离去,许多文化认同逐渐消失而感到惋惜?就在这时,父亲的忠告突然让他警醒:“你是家里的长子,也是一家之主,所有关于泰国的习俗、村里的事、家里的事,你都要了解。别出了什么事,你还要雇别人,你什么都不懂,就成了‘外人’。”
从此,萨姆·文平重新开始学习,从“知道”到“懂”,从只会听到会讲解,摸索着泰国风俗习惯和文化的规律。那时,萨姆·文平的家里有一本泰语古书,但他和家里的很多人一样,不识字。还有一次,他去朋友家玩,朋友也拿出一本用杜纸写成的泰语古书,问他识字吗,请他读给他听。萨姆·文平再次大吃一惊,他意识到自己和很多泰国人一样,不懂泰语。为什么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如此冷漠无情?
再也拖延不下去了,再也不想让自己沉溺于那种漠然之中,萨姆·文平“开始”“挖掘”、收集、提问,阅读、理解和书写泰文。萨姆·文平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在书上看到泰文印刷体的情景,当时他的内心激动不已。就在那时,他在归合区图书馆“发现”了珍贵的“知识宝库”。他说,书籍和报纸再次为他打开了新的视野。在那些日子里,他自认为在区图书馆“打开”了无数的知识,其中,他发现了吴德盛-甘仲编纂的《越南泰族习惯法》。这本书一面是泰文(山罗文),另一面是越南语常用文,讲述了泰国人的教义、婚丧习俗和歌曲。萨姆·文平认真记录自己对押韵和书写规则的研究,然后将其与家乡的泰文文字进行比较。他的勤奋令很多人感到惊讶。他带着纸笔来到田间地头,询问村里、本村的每一位老人,甚至去其他村庄询问泰文文字、泰国风俗习惯以及泰国人的故事。他白天去学习,晚上点灯记事。他向村民讲述自己走访了多少村庄、遇到了多少人、喝了多少酒,收集起每一个字母——民族的灵魂。于是,泰文文字Lai Xu、Lai Tay、Lai Pao、Xu Thanh……被他一个个地发现。学得越多,他就越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幸运的是,由于对泰文的研究,萨姆·文平声名鹊起,并被邀请参加许多国内外泰文会议和研讨会,他意识到,以前只是“井底之蛙”的自己,现在逐渐对泰文有了全景式的认识。
我问他,是什么缘分让他成为了泰国人尽皆知的“三平老师”?他说,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正在田里耕作,有人来看望他。原来是珠强乡(Quy Hop)的一位领导,想邀请他到乡里新开办的泰语班“授课”。他受到鼓励,大胆地接受了邀请。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是区政府官员、乡政府官员以及珠强乡和珠光乡的学生。他成为一名“老师”时,手里没有教材,只是进行一天的教学实践,但凭借着他的热情、他的热情、他的不懈努力以及他日复一日的自我提升,他“克服”了这一切。班上的人越来越多。他说,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泰语在人民对民族宝贵财富的热爱和尊重下强势复兴。
从最初的都城太山罗开始,他便致力于研究编写适合自己地区的泰文教材。《莱岱文》、《莱绪芒函》等成为珍贵的文献,蕴含着他的汗水和心血。继这些文献之后,他又继续研究编写了许多宝贵的文献和教材,如:清化莱文、芒蒙莱文、芒梅莱文、莱宝文、辅音和韵母使用方法等,以及在报纸、杂志和论坛上发表数百篇有关泰文的研究论文和文章。他教授过许多泰文课程,参加过许多研讨会和会议,参与过乂安报民族山区专版“保护古都”专栏,参与过本土知识保护网络……奇怪的是,这些旅行和会议让他渴望重返故地。回归,那是他的归来,作为一个泰国人,因为祖先和亲人而回归,因为有太多需要去发现和命名的事物的召唤而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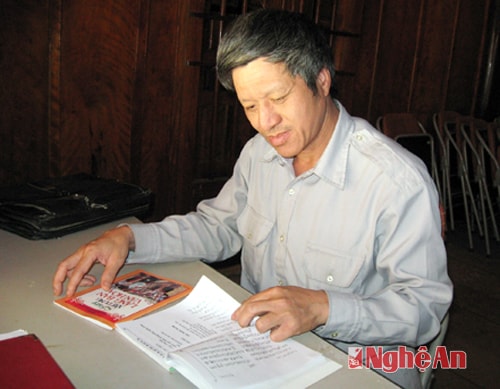 |
| Sam Van Binh先生正在编写泰语教材。 |
他说,多年来他学到的是“不要假设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他确实需要对他所发表的研究进行批评。
我问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泰文吗?他缓缓地笑了笑:“不会。我确信泰语不会消失。有很多人热爱它,有很多人为它充满热情,还有很多人学习过它。我只是害怕失去泰国的风俗习惯。看到这些,我不禁感到难过。喧嚣的生活,强烈的互动,人们的冷漠和疏忽,尤其是缺乏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处于“正义天平”位置的人的不明所以,正在逐渐使泰国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价值消失。我目前正在努力通过祈祷来学习泰国的风俗习惯。幸运的是,我的叔叔去世前给我留下了一大笔“财富”,包括录音带、录像带、照片……记录了他回到家乡,参加宗族、家庭和村庄大大小小的仪式。是他为我奠定了基础,我有责任继续巩固这个基础。”
萨姆·文平说完,便坐下来沉思。他望着窗外斑驳的午后阳光,仿佛想找到笛声、杜鹃鸣叫,以及老僧在招魂仪式上祈祷的声音。难道不是吗?他——森林之子,坐在森林中央,却想念着森林?
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