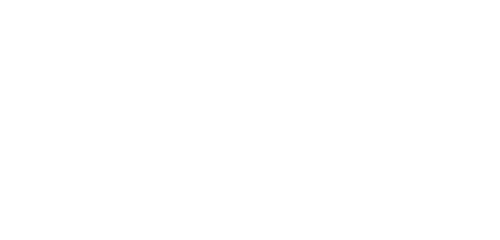短篇小说:《雨之门槛》
又试了两次,小舞终于把薄毯拉到了腰间。夜幕降临,空气渐渐转冷,房间似乎也随之变大了。

又试了两次,小梅终于把薄毯拉到腰间。夜色渐冷,房间仿佛也随之扩大。她蜷缩起身子,感觉夜色像一件廉价破旧的布衣般从她身上爬出来。一阵窸窣声响起,似乎是老鼠在阁楼里乱窜。老旧风扇缓慢的嗡嗡声让小梅感到一阵悲伤;她笨拙地把风扇调到零档。夜色透过棕榈枝,在屋子侧面低语——一种奇特的声音。一阵微风,接着是几阵微风。然后是雨。哦,雨!
梅静静地躺着,倾听着。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雨水如此有节奏地敲打着铁皮屋顶了。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摸遍全身,寻找着旧伤。头顶上有一长串伤口,缝了将近十针,头发被分开,露出一道像旱季溪流一样的白色裂口。手肘上有一道拇指大小的凸起疤痕。额角上,许多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一些细小的印记作为提醒。那些日子深深地烙印在梅的心中,让她感到一阵阵的震惊。
铁皮屋顶的嘎吱声越来越大,仿佛一曲欢快的交响乐,但不知为何,指挥者却全神贯注地演奏着其中一种乐器。夜风呼啸,寒意刺骨,如同她丈夫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小梅身上交叠的伤口。是酒精剥夺了他的人性吗?还是床上的无能让他变得冷血无情?小梅曾深深地爱着他,为他的屈辱和绝望的眼神感到怜悯,他颤抖的手曾触碰过她的胸口,却又果断地移开了。
小梅蜷缩在毯子下,寻求一丝温暖。毯子散发着淡淡的肥皂香。她渴望别的味道,却不得不放弃。孤独时,渴望是一种痛苦却又温柔的痛楚。
我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丈夫过得怎么样。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他?小梅打了个寒颤,仿佛想甩掉所有尘封的记忆。那只流浪猫,那场意外,还有她丈夫性格漫长而痛苦的转变。
这座城市里也到处都是流浪猫,但只能偶尔听到它们的叫声。小梅害怕在夜里遇到它们冰冷刺目的目光,听到它们哀怨的叫声,以及那些离奇却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复仇故事。
小麻衣身材娇小,像一颗小糖果,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垂过腰间,明亮的双眸和甜美的笑容,再加上她活泼开朗、健谈的性格,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她为何如此不幸。“这是颗泪痣,”诊所的一位护士缝合完小麻衣的伤口后,目光紧紧地盯着她说道。另一位护士补充道:“把那颗痣去掉,顺便也从你丈夫的视线里消失。看看他还能做什么。半人半兽,谁会同情她呢?”
小房间让人感到窒息压抑;鼓励别人离开丈夫,尤其是一个半残的丈夫,实在不是个好主意。可是,你必须自救,小梅!她咬着嘴唇,泪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毕竟,这是婚姻的盟约;就这样离开是不道德的。小梅不想让父母担心伤心;他们时日不多了。她决定尽量保守秘密,让双方都满意。
***
在多次抱怨猫咪偷吃厨房食物后,她终于在屋子的角落里放了个捕猫笼。一天早晨,小梅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猫咪蜷缩在铁笼里,吓得她跳了起来。从它油亮的黑色皮毛到它那张小小的、扭曲的脸,小梅分不清那是怨恨还是恐惧。它那冰冷傲慢的眼神让小梅感到一阵恐惧。显然,死期将至,而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小梅想尽一切办法想救它,却找不到任何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尤其正如她丈夫所说,抓一只黑猫——传说中的灵丹妙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梅很快就把猫抛在了脑后,眼前是层层叠叠的梯田、齐膝高的野草、刚从溪流里捡到的几只蜗牛,还有搁浅的黑鱼。她兴高采烈地想象着一碗清爽的蜗牛野菜汤、一盘姜黄炖黑鱼,还有一些水煮野菜。突然,太阳落山了,一团乌云遮住了阳光。抬头望着灰蒙蒙的云朵,梅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便加快了脚步继续前行。
屋子里像个派对,挤满了她丈夫的酒友;邻居尖锐刺耳的声音,隔壁男人娘娘腔般的腔调,还有她丈夫表弟粗鲁喧闹的笑声,交织成一片嘈杂的喧闹。不知为何,一股深深的悲伤涌上心头,梅默默地走到井边去打水。路过火炉时,一口锅冒着热气,锅盖半开着。梅瞥了一眼,差点摔倒。锅里翻腾着一堆肉和骨头,露出一颗剃得光秃秃的脑袋,它紧咬着牙关,露出锋利的牙齿,充满仇恨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梅。
“它只是一只猫,只是一只猫而已,所有生物的生死都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小梅这样安慰自己。但她已经没有心思准备原本计划好的午餐了,那是一顿简单而宁静的饭菜。即使后来,这顿饭的念头也偶尔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热闹的聚会被渐渐减少的酒水和烟草打断了。每当麦的丈夫坐下来喝酒时,他都会喊她一声。他对朋友们彬彬有礼,视他们为贵宾,即便谈话内容只是泛泛之谈。他的呼喊只换来其他人喧闹的谈笑声;麦还在后院给娇嫩的蔬菜除草。偶尔,麦会分神,就像现在这样,脑海中浮现出那只猫的身影,以及它冰冷凄凉的眼神。她坐在那里,陷入沉思,手中的蔬菜轻轻摇晃。微风拂过,带来鸟儿的鸣叫、偶尔的犬吠,以及蝴蝶在枯枝上翩翩飞舞的瞬间。突然,一声巨响和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吓了她一跳。她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被一声喊叫惊醒。她扔下手中的蔬菜,跌跌撞撞地穿过土豆地,越过长满青苔的门廊。只见一个人面朝下躺在地上,摩托车的引擎声依旧轰鸣,屋前的电线杆上沾满了鲜血。小梅惊恐地尖叫起来,她意识到躺在那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她的酒友们围了过来,有的把他翻过来,有的则四处寻找钥匙熄火。小梅瘫倒在地,震惊得动弹不得。
那场事故导致我丈夫半边身体断成两截。他的半个头骨、一只眼睛、一条胳膊和一条腿都失去了功能。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残疾。
几个月来,她的丈夫一度被认为活不下去了,但奇迹般地康复了。然而奇怪的是,当他失去一半基本机能时,却仿佛长出了一张额外的嘴。一旦能够进食,他就开始语无伦次地胡言乱语,仿佛害怕自己再也无法说话。起初,麦很高兴看到丈夫恢复得这么快,但最终,她开始担心起来。
当她丈夫再次开始酗酒时,她的焦虑达到了顶峰。起初,他只是独自在家喝几杯放松一下,后来几个朋友也加入了进来,接着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去世后,经济拮据,小梅听从了一些建议,开始从屠宰场买鸡蛋煮熟出售,以此补贴家用。起初,她挨家挨户地兜售,但最终,她在自家门前安顿下来,摆了几把小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些酒——一个供建筑工人和工人每天晚上回家喝酒的小摊。凭借着精明的生意头脑和一点机智,小梅的小摊总是顾客盈门。一天,一个略带醉意的男人拍了一下她的臀部,吓了小梅一跳。那男人放声大笑,夸她“美味”,小梅气得浑身发抖。
仿佛受到祖先的庇佑,小店生意越来越好。她甜美的笑容和温柔的声音吸引着顾客不断光顾,偶尔的玩笑——有时会让小麻衣脸红——更增添了顾客的兴趣。无论如何,小麻衣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曾经说过,他打了她一巴掌,吼道:“这家伙又不是聋子也不是瞎子!”
吃饭时,他把那盘红烧鱼扔给狗,脸色扭曲,怒不可遏。小梅愣住了,张着嘴看着狗狼吞虎咽地吃着鱼肉碎屑。“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你把五花肉分给大家吃,却让这狗吃鱼肉碎屑?!”小梅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喉咙像被扎了一根菠萝蜜刺一样难受。她丈夫的另一只脚伸进了盘子里;小梅赶紧把脚抽回来,倒了些汤在脚上,然后狼吞虎咽地咽了下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一只拖鞋嗖地一声从她耳边飞过。小梅本能地躲开,转过身盯着丈夫。他举起一根手指,平坦的胸膛绷紧,剩下的那只眼珠子空洞地瞪着她。“我警告你!”
麦收拾好东西,悄悄地离开了。去哪儿?她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街上不乏好人;她也确信自己能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很多人都这么说。她游荡过许多街道,在许多餐馆打零工,却被那些肮脏粗糙的手和嫉妒的无情行径所震惊。她该如何净化自己的心灵?去哪儿都行,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能活下去!摩托车司机坚定的话语和紧紧的车把麦拉回了现实。桥面被风吹拂,过往的车辆回头张望。她紧紧地把包抱在胸前,望着冰冷的河水,浑身颤抖,下巴僵硬,几乎要被冰冷的河水吞噬。
旅馆里住满了工厂工人;他们黎明即出,黄昏才归,洗完澡就直接睡觉。大家都没时间互相打招呼,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明天我带你去应聘。天哪,我不会打扰你家人的!”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回荡。他方正的脸庞,浓密的胡须,还有那双和善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小梅拉起毯子盖住自己,蜷缩起来,试图入睡。外面,雨水依旧倾盆而下,猛烈地拍打着铁皮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