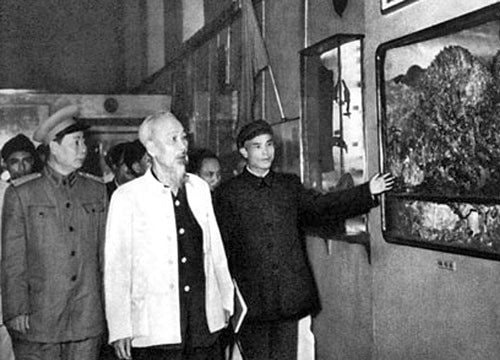我娘家村里的茅草屋
1901年初,母亲去世后,年幼的阮生功被父亲带回了家乡。不久之后,最小的弟弟也相继去世,这让阮生功悲痛万分。祖母和楚阿村成了阮生功和姐妹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在充满艰辛与美好回忆的童年岁月里,守护着他们,为他们提供庇护。
.jpg)
阮生色先生家人的哭喊声惊动了金莲村和黄柱村的村民,他们纷纷前来吊唁。大家都很感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哀悼温柔贤惠、美丽贤惠的阮夫人突然去世。
令这个家庭更加悲伤的是,小欣在从顺化回老家的路上,因渴了奶,又患上了重感冒,不久后也去世了。
阮氏白女士已年过六旬,长女和不幸的孙辈相继离世,悲痛欲绝,但她又必须强忍悲痛,安慰和照顾孙辈。
恩欣的离世,在阮生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深深的悲伤。在哀悼的氛围中,祖孙之间、父子之间、姐妹之间的爱显得更加亲密。阮生功深爱着祖母,帮她做家务和花园里的很多琐事。前花园里的百合花丛总是在他精心照料下,白色的花朵开得格外明亮。菠萝蜜树、槟榔园、桑树埂和香蕉丛,都仿佛成了他姐妹们的亲密朋友。
萨克先生对家庭的不幸深感震惊和不安。为了减轻悲痛,他应邻居们的请求开办了一个班。许多远近的邻居都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学习。家长们从香仁先生家(也在黄筹村)借了几间房子作为教室。辛功的兄弟们仍然可以跟随父亲学习。辛功的中文相当不错。在课堂上,辛功最喜欢练习排比句;谁能写出好句子,就经常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表扬。有一次,在练习排比句的时候,老师出了一句排比句:“白眼”,意思是“白眼睛蓝眼睛”。有的人背对联了,却没有受到老师的表扬。看到班里有一位同学因为眼睛疼,不得不用红布蒙住头,辛宫立刻询问道:“红黑头”,意思是“黑头,红头”。然后全班哄堂大笑。古萨克先生看儿子虽然机灵,但有时太爱玩,不太用功。
每当萨克先生忙的时候,他就会请王树都先生来教他。对辛宫来说,都先生也是他母亲那边的亲戚。他称都先生为“叔叔”。与当时的许多老师不同,都先生几乎从不打学生。他经常向同事们吐露心声:要教好学生,就必须爱孩子如同爱自己。
虽然跟王树都先生学得不多,但阮生宫对他却十分敬重和感激。书中写道:“师出有名,一言抵半语。” 阮生宫先生欣慰地感谢王树都先生多次帮助他授课,为他创造条件,让他有时间思考文学。他的文学之路还未完结。
1901年中,新肃科举考试即将来临,阮氏白夫人不畏年老体弱,答应照顾孙辈,以便女婿能及时进京赶考。
对于阮生宫来说,Trua村是他的出生地,他出生在一座简陋的茅草屋里,在花园里的一片竹林下,那里有他童年的许多快乐和悲伤的回忆:
可爱的 Trua 村里真是一片欢乐的景象,
寺庙上方,井或地形下方。
夏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时候,朋友们常常邀请辛宫一起放风筝。有一次,风筝飞起来转了一圈,就掉在了地里。修了好几次,还是老样子。朋友们都灰心丧气,互相劝说,不如毁了再做一只;但辛宫坚持不懈地修好它,最终,在楚阿村孩子们的欢呼声中,风筝飞上了蔚蓝的高空。
楚阿村有很多池塘和沼泽,钓鱼也是辛昆和朋友们的爱好。一天下午,Thuyen和辛昆正在钓鱼;浮标摇晃了一下,Thuyen猛地一甩鱼竿,鱼钩钩住了辛昆的耳朵,导致出血。Thuyen惊慌失措,大叫起来,但辛昆却镇定地摘了一些菥蓂的叶子,揉碎,敷在疼痛的地方。为了安慰朋友,辛昆不停地说:“没事的,没事的!只要血止住了,就没事了!”

对忠古地区的孩子们来说,最有趣的莫过于在忠山上玩拔河。孩子们喜欢和辛宫站在一起,并非因为他拔河技术好,而是因为他机智过人,总是能赢。而且,即使输了,他也能保持冷静,不骂人也不生气。对于年纪小的孩子,他总是很体贴,不会因为年龄而欺负他们。
阮氏白夫人对最小的孙子非常宠爱,很少责骂他,但也从不让他玩耍。萨克先生回顺化后不久,她就把孙子送到了友璧村(现义安省南丹县南江乡),继续跟随黄潘琼老师学习汉语。课堂在阮仲威先生家的外屋里。辛宫刚学了几天就被老师注意到了。
老师看到辛宫(Sinh Cung)和长子(黄潘京,又名Trong)同龄,学习成绩优异,举止得体,便请求白先生让他住在自己家学习,给自己的孩子树立榜样。Trong和Mong(黄潘善饰)虽然是老师的孩子,但学习成绩却略逊一筹。辛宫的学习成绩更胜一筹,经常在两个朋友面前完成作业、背诵课文。
闲暇时,辛功经常给朋友们讲故事。顺化都城的奇闻轶事让辛功津津有味,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故事。顺化和孟对这位挚爱的朋友念念不忘。半个世纪过去了,辛功依然记得他尊敬的老师和两位同窗的身影。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