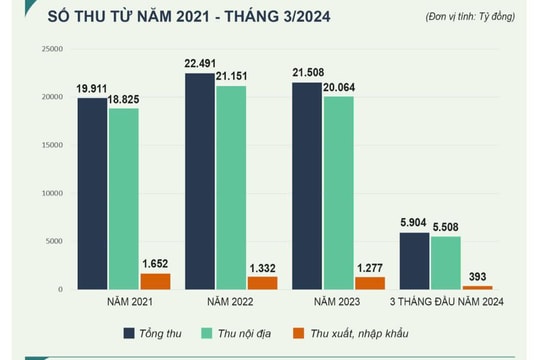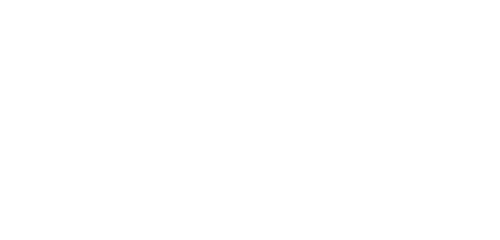“艺术家”
(Baonghean.vn)——“工匠”,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样称呼乂族人,我猜一定是乂族的一位学者。乂族人才济济,他们的声音可以化作音乐,所以乂族的音乐让远道而来的人们铭记在心。
我真的没想到我也是……一名艺术家。
我从过去到现在的背景是:父亲的家乡是承天顺化,母亲的家乡是宁平,在清化市出生、长大并上高中,在顺化上大学,现在在……波来古,与义河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我小时候在清化,只知道开往荣市的火车是路的尽头。广平、永灵,一个遥远、神秘、无边无际的地方,仿佛……另一个世界。我的家就在铁轨旁边,所以坐火车去南方最后一站的梦想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却始终无法实现。每次坐火车,我都去北方。
1975年之后,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三个孩子从清化坐火车到离这里不远的荣市火车站,在那里他们买了一张去顺化的汽车票。那段漫长的等待,任何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也让我这个刚高中毕业的男孩,对荣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原来荣市也是……现代化的,尽管那时的火车站和荣市汽车站24小时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一片混乱,汗水、污水和排泄物的气味,盗窃、追逐、打斗的尖叫声,扩音器的声音,持续不断的警笛声,让人紧张、警惕、束手无策。谁知道呢,在听到火车终点站,然后被美军的炸弹炸得荡然无存之前,我以为这里像……一个偏僻的地方。结果发现它也像……我曾经居住的清化市。不仅如此,荣市的女孩子也非常漂亮。一个正在长腿的年轻人的想象力,让我对在荣市车站遇到的同龄女孩的看法更加开放。一天下午,父亲说,乱吃东西既痛苦又浪费钱,去人家让他们煮好米饭端过来给我们吃吧。
我端着两碗用手帕包着的米饭,沿着铁轨走去。走了一会儿,看到一户人家,点着昏暗的油灯。我走了进去,大声跟房东太太打招呼,她才出现。我解释了来意、情况、目的、意义……她打听了几分钟,说:去厨房做饭吧。
家里只有兄弟俩,做饭简直……洗手就行。饭很快就煮好了。我正费劲地想用毛巾包好米饭带回家或者去问个通知,这时……房主的女儿出现了。
不像现在的女孩子那么活泼敏捷。这女孩害羞得结结巴巴,脸涨得通红,然后说:“抢了带回家。” 没错。我洗了手帕,正要用它抓饭,这女孩却说:“有槟榔。” 说实话,我偶尔也会抓饭,不过是用手帕,从来没用过槟榔。当然,从洗槟榔的方法开始就有点尴尬,要怎么洗才能让槟榔变得柔软干净,于是这女孩……就卷起了袖子。
那是我听过的最甜美的义河方言,虽然说实话,有很多句子我……听不懂。但她的呼吸很轻柔,微微出汗的鬓角似乎在颤抖。在荣市那个阴暗的下午,直到现在我……仍然希望我能回去。我还记得,她在我后面的一个班上……
后来,我在顺化上大学,认识了很多……工匠。毕业工作后,我也认识很多工匠。哪里有工匠,哪里就热闹非凡,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绝无二致,工匠的“特长”就是既骄傲又保守,既自信又霸气,既粗犷又粗犷,既平和又……锋利。
我也和一些艺术家一起演奏。
作家范德龙是安城人。听说他在农村的时候很苦。他父亲是公社主席,但家里很穷,因为他很天真。后来,他的儿子也很天真,甚至可以说是苦行僧。他考入农业大学,毕业后去了嘉莱工作。他等了整整一个月的雨季,心里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写诗。但现在他已经写了十多本书,成为了越南作家协会的成员。在公务员队伍中,他是嘉莱农村发展部的部长,这是一个不小的职位,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个职位。但距离退休年龄还有3年,他突然要求提前退休。除了写作和担任部门主管之外,他非常热衷于创造,从制作鸡鸭鹅等各种鸡蛋的孵化器,到现在每天为人们孵化数千枚鸡蛋,还发明了用树叶治疗和预防家禽疾病的药物等等。
在多乐省,有一位名叫万清的先生,他曾是义安省的中文老师,后来来到邦美蜀写诗。与龙先生不同,他固执己见,而且……没有受过教育。他有两首关于我居住地波来古市边河的著名诗句:“我太想你了,一辈子没有水/死水变成了我的海洋”真的,只有非常固执、持有……负面观点的人才能发现这一点。我钦佩你的智慧。
我第一次见到文如强先生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搭讪,他微笑着摇了摇白胡子,我认出了他。喝啤酒时,他要求倒进……碗里给他。我瞪大了眼睛,他说排长队喝酒更爽。后来,我们走近了,我了解到了住在首都的另一位乂族人。他固执而又节制,鲁莽而又一丝不苟,暴躁而又沉静。他是乂族中极少数说话轻声细语的人之一,即使在酒会上,他也轻声细语,手脚也很少……挥动。“养猪的文如强教授”和他的胡子的故事成了一个轶事,一个传奇。在他身上,保守与解散似乎总是闪烁着,造就了一个非常乂族,又非常越南的文如强。
最累的就是跟黎辉茂先生一起演戏了。这个人是艺术界的名牌,当然少不了陶先生、阮仲焘,就是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艺术歌曲《歌谣歌》的那两个人。
有一次我去河内开会,借了辆车,邀请黎辉茂先生来清化——我之前撤离到那里,几十年没回去过。我提前通知了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准备了非常真诚隆重的欢迎仪式。老同学们都被叫了回来,公社书记也请来了。进门后,我和朋友们感人地拥抱了一下,然后自我介绍:我是诗人黎辉茂,《曲词歌赋》的作者。我立刻……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大家都把黎辉茂团团围住,五七个人拿出手机证明自己手机铃声是《曲词歌赋》,还有人打电话炫耀自己和曲词歌赋坐在一起。然后就这样……半辈子都在不停地徘徊,在开会的时候,一边打电话,一边假装……
诗人阮仲涛在我读我的第一本诗集之前就为它写了序言,但当诗集付梓后,他重读了一遍,说“原来我是凭直觉写的”,果然如此。我是个晚辈,很尊敬远在他乡的哥哥,但他总是冲过来靠近我。他很喜欢来我家“捉燕后”。燕是我妻子的名字。如果要评选越南乃至全世界最能“静坐”的人,那一定少不了陶先生。陶先生能从早上坐到下午,然后“振作起来”,从下午坐到早上。我在波来古的家就曾多次这样接待过他。我身边的人,阮翠卡……要么昏昏欲睡,要么完全瘫倒在地,但他依然稳如磐石。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最近,他中风了,整个义安省都在担心他,是切实的担心,是具体的担心,不仅仅是像观众、读者那样担心他们敬爱的音乐家和诗人。大约半年后,他奇迹般地康复了,恢复了正常的活动,当然,手里还拿着一杯水。然后,差不多一年后,他又病倒了。但我还能在Facebook上看到他的照片,还能看到他摇摇晃晃的样子。生活就是这样,乐观地生活。我似乎从未见过陶先生如此悲观,“义安先生”就是这样……
但后来,他还是没能抗拒命运的安排。在春节前一个多月,他去世了,享年72岁。可以说,从来没有哪场葬礼像他的葬礼这么奇葩。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名字还在Facebook上随处可见。之后,他的葬礼更是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副总理到部长,从作家到读者,不一而足。许多人都惊讶地感叹:原来阮仲陶真的“非凡”,直到他去世,才意识到他的名声、人格、才华和人性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么可怕?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人的去世能如此震撼社会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人强迫他。就像陶先生自己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去世后会有这么多的爱人……
就在义安省的黄梅镇,我也有一位“挚友”。我用“挚友”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虽然素未谋面,却关系密切。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人们有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交流方式。这位男士玩Facebook,是我的Facebook好友。他说他喜欢读我的书,并邀请我来义安省时去黄梅镇看看。重要的是,他强调我是黄梅镇的居民,600年前的祖坟就起源于黄梅镇。我们一直在Facebook上聊天,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是黄梅镇的一位“重要人物”。我钦佩这位男士对时事、对人事极其灵活和负责的看法,尤其是他是一位玩Facebook玩得“疯狂”的“重要人物”。虽然我认识很多玩Facebook的“重要人物”,他们玩Facebook是为了工作,为了掌握社会信息,为了贴近民众,了解民众。更为特别的是,他非常热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已故历史教授陈国王在世时,曾看着我,眯着眼睛,举起啤酒杯说: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占族。占族精髓。
我本来想进一步询问他以澄清情况,但他去世了。
后来,我收到范氏家族的来信,通知我范氏家族在义安省黄梅县的宗祠正在修建中。在落成典礼上,范氏家族的后代们被邀请前来参加。之后,越南范氏家族召开了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曾多次与范如强教授约好一起回去拜谒宗祠,但教授却在临行前去世了……
现在我正式知道我也是一名艺术家,艺术家先生。
得知这些确凿的信息后,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600年前,我的Van家族分裂成了两支,一支北迁,这很奇怪,因为越南的历史就是一部南迁史。北迁的那支如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那就是Van Tien Dung将军家族。其余的家族则按惯例南迁。在清化,我的姓氏很少见,无论我走到哪里提起它,人们都会注意到。现在我来到了南方,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家族,从广治一直到隆安、朔庄、薄辽……Van家族的后代们正在组织起来……互相寻找,每年都会去黄梅县拜谒祖先。Van家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兄弟,但非常重视自己的家族血统,他卷起袖子,为家族承担了六七成的家务,他就是Van家庙的“守护者”,Van Minh Phung。这位兄弟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走遍全国各地寻找范家人……
“艺人”,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样称呼乂族人,想必是一位乂族学者。乂族人才济济,他们的声音可以化作音乐,所以乂族的音乐让远方的人铭记在心。在知道自己也是乂族“人”之前,有一次出国旅行,我费尽心思地把一大堆越南歌曲拷到手机里,准备在异乡听。到了那里,我惊讶地发现,我拷的歌里有四分之三都是乂族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