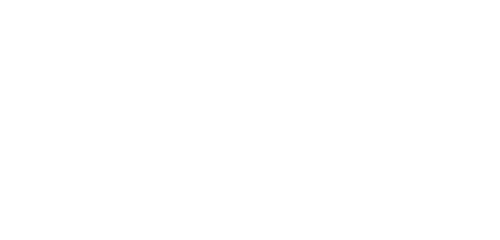远离家乡的义安人使用的义安语
(Baonghean.vn)——每个远离家乡的义安人心中,似乎都怀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那里承载着许多古老的故事。当一个身处异乡的义安人遇到同胞时,他们会立刻问:“你来自哪里?”所有拘束的距离仿佛都瞬间消失。

通往义安的道路蜿蜒曲折(照片摄于剑桥)。纪实照片
我至今仍记得这样一个故事:1981年冬日的一个傍晚,我走在如今的塔光宝街(Ta Quang Buu Street)附近的大古越街(Dai Co Viet Street)旁,听到前面一群理工学院的学生在谈论他们的义静朋友。他们说:“义静的朋友真是好朋友。说来也怪,他们平时跟我们说北方方言,但只要旁边出现一个操着义语口音的人,他们立刻就换了口音,简直不可思议,就像在说外语一样。” 四十多年前在街上听到的这个故事,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更加为义族同胞远离家乡时的亲情感到骄傲,也让我更加为义语口音在外地人听来时如同外语一般而感到自豪。
之后,我于1982年至1990年在柬埔寨教越南语。我记得1983年,我结识了一群越南志愿军士兵,他们当时正在守卫越南志愿军的前线指挥部。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们都是义安省的士兵。在一次啤酒聚会上,我得知这里大约有200名义安省的士兵驻守。这群人中有一个名叫顺的男孩,来自我的家乡——清章县清祥乡永安村,他经常来看我。他说,清灵县还有一个人住在离我15公里远的地方。一个周末,一个来自清灵县的男孩突然来到我家,说:“我是清灵县的云。我从顺那里听说,清灵县有个叫南的人在金边医药大学教书。我想过来看看你。”我本来想借他们的自行车,但是车坏了,所以我就走上来了!
我被那位年仅20岁的年轻士兵深深打动了。一天清晨,他步行15公里,只为拜访一位素未谋面、只闻其名的同乡。Van陪了我一整天。之后,我们偶尔会遇到其他三四位来自清章县的士兵,比如Thuan、Khanh……我记得,春节期间,Van休假,他帮我把信和礼物带回乡下,送到我母亲和妹妹那里,还在我家吃了顿饭。回来的时候,他还带回了我母亲为我做的蜂蜜蛋糕。1984年旱季的一个周末,一位来自同一家乡的士兵,为了寻找像我这样的同乡,步行15公里,这一幕至今仍让我铭记于心,让我感受到他对故土的热爱,以及他对义安人民的深切关怀。

义河方言是中部方言的一个地区分支。在乡间妇女家门廊上,一边享用着槟榔和绿茶,一边讲述着生动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乡村的灵魂和爱意。照片:曹东
2017年,我到巴黎狄德罗大学(法国)工作。一位名叫阮盖乔(Gai Joé Nguyen,越南语名字是Gái)的越南教师,是越南社区的一名越南教师,她曾是我的学生,参加了每年八月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在河内联合举办的“海外越南教师越南教学方法”课程。她带我游览了巴黎。
她知道我来自清章,就给我的一位好友打了电话。这位好友曾和她一起在岘港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嫁给了一个比利时人,现在住在法国东北部的隆维。这位好友名叫南,和我一样来自清章。女孩打电话来说,清章有一位名叫南的老师在这里。当时我们正站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一座桥上,她把电话递给我,让我和南通话。电话那头传来浓重的清章口音,我也跟着模仿起了清章口音……
聊了一会儿之后,Nhan邀请我去她位于Longwy的娘家做客。我说过几天等我妻子过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和我丈夫会一起去。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觉得去不了,因为Nhan家离这里太远了。但机缘巧合之下,我表妹的姐夫,也就是我表妹的丈夫,当时在比利时-卢森堡担任大使,而我表妹通过Facebook得知我在法国工作,于是她给我发短信,邀请我去比利时玩。
和女孩商量后,她提出了以下计划:周末,她和她妈妈会和我们一起去Nhan家,她家位于法国、卢森堡和比利时三国交界处。我们会从昨天下午开始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早上我们会去Nhan家附近逛逛,下午我们会去卢森堡待大约三个小时,然后在卢森堡火车站告别,之后我和丈夫会去比利时。这样我们既可以去Nhan家,又能了解另一个国家——卢森堡。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去了一趟朗维。

义安省精彩纷呈的乡村节日。照片:Trung Ha
隆维地区因其沃邦设计的堡垒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隆维位于洛林地区,靠近比利时边境,比利时是色彩绚丽的“掐丝珐琅”陶瓷花瓶的故乡。Nhan一家四口:丈夫是比利时人,名叫Soblet Dominique,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名叫Ngoc Anh Océane,那年11岁;儿子名叫Ngoc Bao Kylian,那年9岁。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Nhan的两个孩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带着清州口音,尤其是Ngoc Anh。当我听到Nhan对Ngoc Bao说:“你为什么这么懒,不肯说越南语?如果你不跟我学,越南语说得不好,我就不让你去看望你的奶奶和姑姑,听到了吗?”时,即使身处法国的偏远地区,我也感觉家乡离我如此之近。
那次旅行的回忆美好而温馨。众所周知,Nhan的丈夫是比利时人,非常体贴。除了新冠疫情,他每年都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妻子位于清章县同文乡的家乡住上一个月或几个月。彼此熟悉之后,在2018年和2019年,Nhan一家返回义安省时,都会在回乡前顺道来我家住几天。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段Nhan的侄女在我家用义安方言跟我说话的视频。我问她:“你喜欢去同文吗?”她回答“喜欢”;我又问:“为什么喜欢去同文呢?”她回答说:“因为你奶奶和姑姑在那里。”

祖母和孙子。照片:Quoc Dan
2020年,我去韩国教了一年越南语。有一天,我去大使馆开会,碰巧遇到了一个在首尔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越南代表。听到他那浓重的义州口音,我们立刻就聊得火热,之后我们经常周末去他家喝酒聚会,因为他家又大又漂亮。回到河内后,有一天我联系了Thang,邀请他去白梅的一家餐厅喝生啤。Thang骑着摩托车来了,还带了从乡下回来的母亲。Thang说:“带你妈一起来玩吧。”我当时很感动。她就坐在那里,开心地笑着,吃着花生。
我讲述这些回忆,是为了说明对于义安人来说,远离家乡就像是第一个情感信号,它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帮助远在他乡的同胞迅速建立联系。或许正因如此,音乐家黎春花才为诗人梁克清的一首充满义安风情、歌名意味深长、饱含深情的诗歌《义安之声归来》谱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同胞对义安没有感情。事实上,义安人做事往往全力以赴,或许比其他地区的同胞更加执着,因此他们也被戏称为“疯狂”和“极端”。然而,凡事过犹不及。重要的是,远在他乡的人们能够保持对家乡的认同感,彼此之间保持亲切友好的关系,但不要让这种关系演变成小团体、地域歧视,最终沦为“地方主义”。
就语言而言,历史语言学家认为乂语是研究越南语迁徙和发展的重要资料来源。乂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代越南语、古代前越芒语的“沉积”,甚至包括前越芒语尚未与孟-高棉语系分离时期的语言特征。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发现有些高棉语词汇与 Nghe 的词源相同,例如 Khmer:尼斯,Nghe方言:ni越南语:这;高棉语:今天,Nghe方言:正确的越南语:天;高棉语:青盖,Nghe方言:困越南语:遥远;高棉语ch'hô恩格方言站立但与这个词有关小市场(蹲也就是说,这种类型坐姿和站姿),越南语:站立发现这个词的人ch'hô具有与元素相关的含义小市场在坐下来聊天精通乂方言的学者潘玉也是乂族人。1985年我回到河内时与他会面,他非常高兴地向我展示了他发现的乂方言类型。坐下来聊天在我的侙族方言中,它的意思是立即坐下和站起来。蹲, 不是坐在地板上与这个词有关ch'hô他用高棉语说道。他一边笑着一边拍着大腿,显然是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告诉我:“我喜欢跟你讲这个故事,因为你知道义语。这里的士兵们听不懂,所以他们不愿意听。”
尤其在语调方面,我听到和看到很多句子,它们的语调与越南语(Nghe An)和高棉语的语调非常相似。或许正因如此,我学高棉语非常容易,当我讲高棉语时,很多柬埔寨人都说我讲得像母语人士一样。

位于清水乡东丹灌溉湖畔的蜿蜒公路是清章县乃至乂安省最美的公路之一。照片:辉秋
乂安语(乂安方言)是自古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越南语的某些成分仍然保留了下来,但词汇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古代乂安人称:熊现在称为米旧电话鹅, 已经狗现在很多地区仍然被称为狗有些地区被称为女儿作为通用语言。
我遇到的大多数远离家乡的义族人都有很强的口音变化能力。例如,编辑Diep Chi、Quang Vinh、主持人Khanh Vy(他们的口音在北方和北方、南方和义族之间变化很大);有些人虽然口音有所改变,主要是义族口音,但仍然保留着义族人定居地(北方/南方)的口音;还有一些人,无论走到哪里,口音都不会改变,或者说根本无法改变,只会说一些常用词。我有一位亲姑姑(来自清章县),现在她和她的叔叔都去世了。尽管她一直跟着我的叔叔(来自都良县)四处奔波,并在1954年后定居河内,离家六十多年,我的姑姑仍然保留着她的义族口音和古老的义族词汇。我记得有一天我去陈兴道街姑妈家,她看到我进来,她家的猫就惊慌地跳来跳去。姑妈说:对不起(这只是个玩笑)。哦,这个词污渍我已经几十年没听过这个词了,但奇怪的是,我的童年记忆却总是随着这个词涌上心头。污渍我妈妈说的。
总之,每个远离家乡的义族人心中,似乎都怀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那里承载着许多古老的故事。比如,虽然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但依然鲜活的渡口;还有村堤上月光下的歌谣;以及如今也已成为往事的船夫们在林江上划船的身影。当一个远离家乡的义族人遇到同胞时,他们会立刻换一种语气问道:“你来自哪里?”,一切客套的距离仿佛瞬间被打破。
这是正确的:
在陌生人群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握手好吗,先生?
我们家乡浓郁而深沉的口音
我家乡的声音朴实而动听。
故乡的声音在记忆中重现
一旦见面,就很容易互相了解。
彼此相爱,找到“同胞”这两个字……
(歌曲《艺术家的声音回归》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