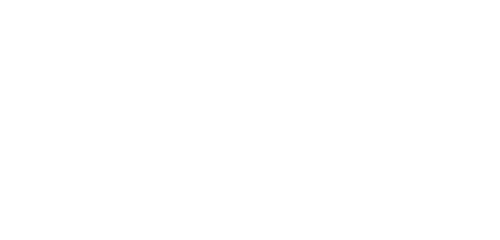苏联人诞生于义静省。
1930年3月18日,三个共产党组织合并后,越南共产党中央局在中部越南成立,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号召群众站起来争取减税、反对强制购买酒类和鸦片、反对殴打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等实际权利……
1930年5月1日,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全国人民斗争的精神,中央地区委组织了荣市义安省工农示威游行,约1200名来自郊区村庄的农民与数百名城内工人协调参加了游行。

示威者挥舞着镰刀锤子红旗,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要求减税、加薪、缩短工时,游行穿过城市……示威者从荣市出发,一路游行至滨水,意图吸引更多工人加入。殖民政府立即命令警察和秘密警察使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他们直接向人群开枪,造成6人死亡,18人受伤。就这样,在义静省的第一次斗争中,革命群众与殖民警察之间爆发了血腥冲突。
当天,法越小学青章小学100多名学生在县城组织集会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与此同时,来自汉林、拉莫和德润村的3000多名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收回被法国殖民者没收的土地,这些土地此前被阮长远(又名奇远)没收。奇远被群众斗争的力量吓坏了,被迫躲藏起来。农民们立即冲进他的住所,烧毁了他的所有种植园和房屋。两天后,殖民政府派遣一队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前往汉林村,调查并“镇压共产党叛乱”。1500多名农民再次包围了这队士兵,抗议殖民政府的镇压措施。士兵们向抗议者开枪,造成18人死亡,17人受伤。
国际劳动节的斗争以流血冲突告终,使义静省群众斗争的气氛空前高涨。中央省委决定利用这一势头,将运动推向更高层次。中央省委宣传机关报《工报》于1930年5月2日发表声明:“安南的斗争迎来了决定性的日子”,号召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效仿滨水和清章的斗争榜样,继续站起来战斗。在1930年5月的剩余几周里,荣市和滨水的火柴厂、锯木厂、SIFA公司、长氏火车修理厂等地的工人持续罢工。1930年6月27日,荣市红色工会组织了来自荣市多家工厂的1000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

为了将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度,中央委决定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和红色工会干部到各县加强党和红色农民协会的建设,动员群众起来斗争。1930年6月1日,清章县3000多名农民再次举行抗议,要求减免赋税、废除巡逻任务,并赔偿在五月事件中伤亡的人员……
抗议者游行穿过区政府,随后在罗市场举行集会。由于惧怕群众的力量,清章县长不得不前往罗市场接收请愿书,并承诺向上级汇报。第二天,来自安山县和宜禄县的2000多名农民也在区政府门前抗议,要求延期纳税,两县县长被迫让步。6月18日,南丹县约600名农民举行抗议,随后在敦市场举行集会。南丹县长试图逃跑,但被民众抓获,被迫接受了群众的请愿书。
中央党委和各省党委大力指导地方党、工会、农民协会基层动员群众,准备开展一场新的、更加激烈的斗争。1930年8月30日,在基层党员干部的领导下,3000多名南丹农民举行抗议活动,在多地组织集会,随后游行至沙南镇,捣毁了丰丹酒行,冲击了区政府,焚烧了所有文件,闯入监狱,释放了囚犯。南丹区长黎克祥被迫与群众见面,并在请愿书上签字盖章,承诺“南丹区长今后不得再骚扰人民”。此后,抗议者蔓延到各公社和村庄,焚烧哨所,镇压地方官员和村长。
1930年9月1日,清章县爆发了一场约有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农民示威游行。为了镇压示威,清章县长潘士邦下令士兵向人群开枪,造成一人死亡。示威人群立即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上前去,县长和士兵仓皇逃窜。民众冲进县政府大楼,将其占领,并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潘士邦的私人住宅。
8月30日和9月1日的抗议活动之后,南丹和清章两县的殖民政府垮台或彻底瘫痪。1930年9月6日,《老乡报》特刊报道:“在清章和南丹,无人缴纳市场税,也无人敢收税。无人巡逻,士兵不再驻守。帝国主义被镇压和摧毁,无人执行。我们赦免了民族罪犯,将奇园种植园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我们可以自由地结社和示威游行。就这样,帝国主义的法律被粉碎了。”
在义安省农村殖民政府垮台的情况下,尽管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村里的红农会执行委员会(简称“红农”)不得不承担起农村的行政和自治职能。这标志着越南第一个革命政府的诞生。

1930年9月1日,荣市红色总工会响应农民运动,在多家工厂数千名工人的参与下,发起了一场总罢工。中央省委和义安省委的传单随处可见,号召人民效仿清章和南丹农民的榜样,奋起反抗。如同连锁反应一般,群众的强大斗争彻底瓦解了加河两岸大部分地区(安山、都良、宜禄、雄原)的殖民封建基层政府,并将斗争蔓延至高地地区(昆强县的门山、陆大)。
1930年9月8日,安山县7000多名农民举行抗议游行,前往县政府提出诉求。法国殖民者两次出动飞机轰炸抗议者,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杜良驻军的士兵也奉命向抗议者开枪,造成数人死亡。抗议者被迫解散,但在9月10日晚,在为死者举行悼念仪式后,民众分散开来,惩罚了县长和各村村长。安山县各村的殖民政府瘫痪,并逐渐瓦解。
1930年9月12日,在雄原县,8000多名农民聚集在党旗下,手持棍棒、镰刀、肩杖、砍刀,敲着鼓,游行至安春火车站,封锁了火车,举行集会和演讲,然后返回县城。当抗议者到达泰老时,法国殖民者派出两架飞机向人群投掷炸弹并开火,同时命令士兵冲出并用武器驱散抗议人群。当天下午,当人们前来埋葬死者时,法国殖民者再次派出飞机投掷炸弹,造成更多人员伤亡,使得9月12日雄原县的死亡人数达到217人,另有125人受伤,多人被捕,277间房屋被烧毁,禄州村和禄海村被彻底摧毁。这是法国殖民者在亚洲和非洲整个殖民历史上镇压最残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法国殖民者镇压越残酷,义安省人民的斗争运动就越发高涨。1930年9月和10月,义安省每天都爆发数十场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震动全省。9月初,群众示威运动也迅速蔓延至河静省。9月7日,1000多名干禄县农民手持棍棒、长矛、鼓、号角和锣,抗议并占领了县政府,焚烧所有文件,释放政治犯。第二天,河静省各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虽然河静省的运动爆发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各地民众抗议、占领县城、惩处地方官员、驱逐军队。短短几周内,河静省农村地区的殖民封建政权似乎就彻底垮台了。
1930年9月底,《共銮报》对义静省的局势描述如下:“在村庄里,村长和乡长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力,无法掌控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印度支那总督罗宾在一份发往法国的报告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他们完全无能为力,无法阻止运动的蔓延。省内各级地方官员都处于瘫痪状态,既无法任命任何领导人,也无法依靠乡和公社当局的任何帮助,这让民众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被统治者的所有权威。官吏们也陷入了恐惧之中,他们锁上大门,躲在家里,只顾着自保。每次县长和乡长与军队或地方士兵一起巡逻时,他们都浑身颤抖。”

尽管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和准备,但当义静农村的殖民封建政府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瓦解和瘫痪时,村里的红色农民协会(在一些地方被称为Ban xa hoi)承担起了管理和运作职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
在经济方面,人民公社农业部将公有土地、资金和粮食重新分配给农民,并停止向殖民政府缴纳税款。数千公顷被当地官员非法侵占的公有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村民。人民公社农业部还迫使当地官员将征收的税款返还给人民,迫使债权人延期偿还债务,并迫使地主减租25%至30%。革命政府还高度重视灌溉系统的整顿,组织修建水坝、开挖沟渠、抽水抗旱。在一些“红色村庄”,例如义安省清章县上寿村和河静省锦川县富越村,乡农业厅征用公有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集体生产:共同耕作、收割,并按工作日分配,公共资金用于共同用途。其他一些地方则合并并建立了更多的耕作、种植和盖屋顶的合作社,以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扶持。
政治上,殖民封建政府已经崩溃。夏博农不仅宣布废除殖民国家和南朝的法律,也废除农村的法律和习俗。历史上第一次,整个传统的政治制度,连同等级制度和诸多歧视都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群众创建并得到人民全心拥护的全新社会政治秩序。革命政府采取措施保障村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例如享有受教育的自由,在婚姻和所有社会家庭事务中实行性别平等。红色自卫队成立,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村庄安全。与此同时,夏博农也挺身而出,调解或裁决村里的纠纷和诉讼。

义静省农村地区乡级农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发展革命力量。白天,除了组织生产活动外,农民群众还被动员起来参加数十场集会和示威游行。晚上,村民们聚集在村公所,听党政干部宣读报纸,讲解新政府(现在被称为苏维埃政府或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积极加入红农会、妇女解放会、共青团等革命组织和团体。其中,红农会是村民自愿加入最多的组织。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要组织一个农民协会,只需敲响公社的鼓,邀请村民参加。动员委员会宣读并解释规章制度。任何同意的村民只需举手加入。很快,农民协会就成立了,执行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
在有利条件下,当革命运动达到顶峰时,革命力量也发展得非常迅速。1930年初,在义静省,越南共产党只有约300名党员,而红色工会和红色农民协会则组织了1000多个群众组织。到1930年底,仅义安省党委就有188个支部,2011名党员;红色农民协会就有48484名党员;红色工会也有399名党员;此外,共青团有2356名党员;妇女解放协会有8648名党员。
在文化方面,革命确实给“红色村庄”带来了崭新、健康、进步的生活。许多在村庄里流传数千年的陋习被废除,就连偷盗、吸食鸦片、赌博、算命、拜鬼、食用肉类、节庆活动等社会弊端也被废除或自动消失。婚礼、忌日、葬礼,甚至农历新年,都以一种新的、更简单、更省钱、更便捷的方式举行。妇女联合会成立了产妇互助小组,在分娩时互相帮助。尤其是在“红色村庄”,公社农业部门为村民组织了许多免费的民族语言课程。革命政府统治下的村庄里,气氛激动人心、热情洋溢、充满喜悦和自信,甚至带有一丝浪漫主义色彩:“当时最常用的名词就是‘社会’。许多人忘记了工作,相信革命即将成功,一切都将属于社会……”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