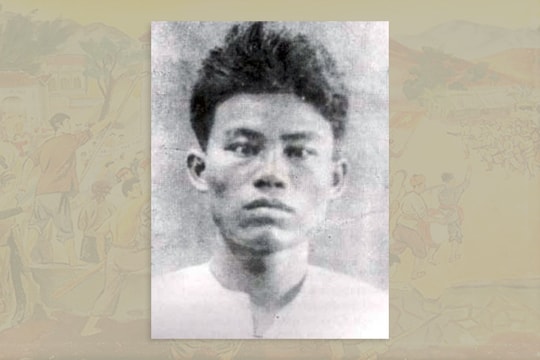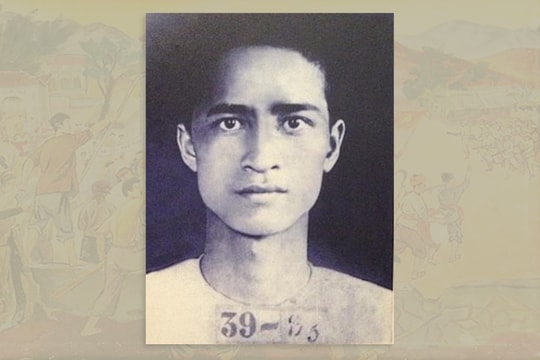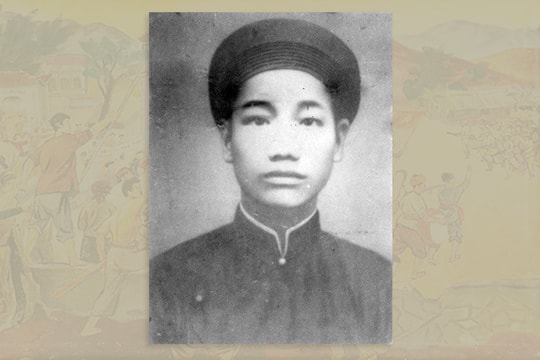用泰语和老挝语见面
泰寮烈士纪念碑(位于兴原县泰寮镇)的所在地,是为了纪念1930年9月12日义静苏维埃运动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庄严树立的。这座纪念碑以前被称为“丹雅汉”(Dam Nha Hon)。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丹雅汉乡村地区在民间传说中常常是充满灵性故事的土地。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圣地,成为革命斗争传统的象征……
正午时分,烈士纪念碑前,烈日炎炎,人们正忙着为英雄烈士们举行追悼会。我问正在架梯子挂追悼会横幅的蓝衣男子:“您是哪家的?”他回答说:“我是泰寮人,我家就在街对面!”“应该好几代了吧?”他擦了擦汗,看着我:“谁会来?法国人炸死示威者的时候,这里还是稻田;抗美援朝初期,这里还是稻田。如今这里发展起来,我成了泰寮镇的居民,大概也是承蒙英雄烈士们的恩赐吧!”
见他对故事不感兴趣,还一直琢磨着他那份认真的“感恩”,我便溜达进兴原县人民委员会,与文化部门的几位工作人员见面,聊起了泰寮从村子、乡镇到如今的县城的土地和人民。我拿起那本近900页的《兴原文化地理志》,只用大约两百字提到了烈士纪念碑,其中包括这样一段话:“1930年9月12日清晨,217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泰寮乡的田野。那些阵亡的、仍被亲属确认身份的烈士被运回家乡安葬。其余大部分烈士都葬在丹雅汉(Dam Nha Hon)的集体墓地里。这里后来被国家修建为泰寮烈士陵园。1956年,乂安省将其修建为泰寮烈士纪念碑遗址。”
 |
| 泰国老挝烈士纪念碑全景。 |
无论名称或规模如何,都难以传达那英勇而悲壮的一天的意义。我去了老教师陈文迪的家。他出生于1924年,原籍义烈乡(现兴林乡),被认为是该镇的新居民。我想象着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九十岁、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想象着1945年被越盟任命为兴原起义总司令的年轻人陈文佑。老师说:“是啊,这里曾经是一片田野。现在的199号公路不像现在这样笔直,但到了兴通桥,又弯弯曲曲地回到了现在的市中心。就是那一天,数万名兴原农民的示威游行沿着46号公路已经延伸到省会很远的地方时,法国人惊慌失措,扔下了炸弹。”
我在研究和撰写兴原县历史时,接触到了一位指挥那场血腥镇压的法国军官的证词。他说,当抗议活动像决堤的堤坝一样时,即使飞机在头顶飞过,也吓不倒他们。他们的主子怕兴原农民下来毁掉兴原县府,然后冲下去占领荣市,所以下令投下炸弹,派军团士兵用机枪阻拦……”当时,Dieu 老师还年轻,但他的父亲,老革命家陈乔目睹了那场大屠杀。陈乔那一代人还没有赢得或保持斗争的成果,而 Dieu 那一代人却已经发动了八月革命,成功夺取了政权,这或许是得益于先烈英灵的支持?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历史记录了那次事件中牺牲的 217 人,但在泰寮烈士纪念碑的纪念碑上,却只刻上了 114 个人的名字?
迪厄老师清楚地告诉我,受九一二事件的影响,阮爱国向共产国际报告,承认印度支那共产党支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从此,兴原县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运动空前高涨,为八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1961年,胡伯伯第二次回乡时,也特意到泰寮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上香祭奠英雄烈士。
84年过去了。那一天,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泥泞的田野,如今,这些村庄的田野上,都是玉田、赤涅和安瑙三个村落,它们如今已成为泰寮镇的组成部分。然而,最初,自1956年制定兴原县的政策以来,选址的地点是泰寮(现属兴道县)的泰舍村地区,该村原属泰寮,与现在的规划区相距数公里。后来,由于一些问题,该镇不得不解散,重新规划,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以泰寮乡赤涅村为中心。这意味着,繁华的市中心终于迁往泰寮烈士纪念碑,与神圣的遗迹相拥相聚。
住在泰寮4号楼的泰辉碧老师——县老教师协会主席——还没吃午饭,他不顾我此时打扰他的愧疚,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的实地考察成果,以及对兴元县一个古村落的文献研究。他得出结论:旧泰寮乡泰舍古村落(现兴道4b村)的土地就在康兰田野一带,那里至今仍留有遗迹和轶事。那里还有阮惠光宗时期第五组胡世越先生的陵墓(裴阳历博士所著《义安基》一书中写道:“阮惠兄阮汝(阮汝)说,阮惠光宗时期的第四组就在那里”)。荣市国民学校前校长勒布雷东在其著作《安静古律》中写道:“东泰村(字面意思为泰夏)位于大海山南麓,是西山氏族的发祥地。” 书籍和史书是大事,我不敢妄加评论,但说实话,今天的兴原县必须拥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回响,需要加以肯定、唤醒和弘扬,与泰寮烈士纪念碑这一神圣的革命地址一起,打造出一个拥有深厚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骄傲。
泰寮镇中心的十个街区,如今属于古老的池尼村。在苏维埃运动的英雄岁月里,池尼村被认为是最繁荣的村落。这个村子原本坐落在一片低洼的田野上,故历代儒生将其命名为池尼,意为“香泥”。隔着一条船来船往的河,便是玉田村,因村内有白千层树守护着碧绿的稻田,白鹳栖息,景色秀丽如画,故古人以“守护田地的明珠”之意为其命名。玉田村过去曾有造船作坊,甚至可能还有战船,因此历代封建王朝从邻村招募的士兵,都是水兵(据潘辉碧老师考证)。
池奈村,又称柯奈,原由胡、桐、奇、柯饶4个村组成。桐村有一座义庙,供奉“当地桐山神将胡本”,是胡家的神祇,有杀虎之功。胡村有一座大型庙,供奉村里的守护神,至今仍保留着祭祀规矩:“除春秋两季祭祀外,每三年,每户要备一粽子,每男丁出五钱,买牛、牛、猪等祭品。全村祭祀完毕后,按男丁的份量分糯米饭和生肉,与家人一起煮。只有达官贵人和仆人才能在庙里吃喝……”。古村落、古塔虽已不复存在,但村名、地名犹在,为泰寮土地增添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泰寮古城历经数个时期的改造、建设和发展,如今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建筑群规划合理,交通便捷,方便前往县内各区域;规模宏大、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碑、省级历史遗迹玉田寺正在修缮和修复,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陵墓传说、光忠国王祖先在泰山的起源、雄道山上的康兰田,共同使该镇成为连接荣市和金莲-南丹两大省级重点旅游目的地的朝圣旅游“纽带”。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了不辜负祖先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努力!
于是,我安慰自己,说我已经“解开”了泰寮烈士纪念碑上那位蓝衣男子的部分陈述。一个区镇规划的迁移原因,有时只有身处当时境遇的人才能理解,或许与时间、空间、历史或文化的解释没有太大关系。但对于1930年9月12日那些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在今天的后人的心中,都源于感激和自豪,因此,人们开始产生崇敬的精神追求也就不足为奇了……